一个学汉语的孩子
 |
|
|
马晓飞是我的学生,是我所任教的语言学校汉语班的一名特殊学生。
我居住在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科希策,人口不足30万。我在国立语言学校开设的汉语班是全市唯一的学习汉语的课堂,每年招收有一定英语基础的中小学学生和成人组成一个混合班。之所以说马晓飞特殊,是因为他只有六岁半,却坐在成人和高年级学生为主的课堂里。
新学年的第一堂课,传达室的伊万阿姨领着这个小男孩进教室,把他抱到了椅子上。看到这个一脸稚气的小男孩,我心里多少有点打鼓。
每年新学年开始,我要了解每个学生的基本信息,给每个人起个中国名字。我根据小男孩斯语名中“马”的谐音,给他取名“马晓飞”。
上了几堂课以后,我就发现马晓飞是这个班一个不小的麻烦。让一个还不会用母语写自己名字的小孩,坐在成人班的课堂里学“外语”,只能说当初我和学校都欠考虑。在最初的几节课后,马晓飞就不再“听讲”:把笔盒里的每一只铅笔用转笔刀削一遍,下课后留下满桌子的铅笔屑;用铅笔在书本上乱画,再用橡皮擦擦掉,橡皮擦和笔轮番掉地上,从椅子上下来,爬到桌子下找橡皮、找笔,这一套上上下下的动作持续往复。我知道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向校长明确表示我不想要他。但校长和伊万阿姨都说:“孩子学汉语的兴趣很高,而且家里把一年的学费都交了,我们也不要求他学到什么程度,不用参加考试,就让他坐在那儿混着吧。”
每次上课,我得时不时地走到马晓飞身边,把课本翻到当页,再把他的手指放在正在领读的词上,但读到第三个词他的手指就跟丢了,他不认识数字,找不到页面,也听不懂我所讲的内容,常常是从一开课就盯着后墙上的钟表问“老师,还有多长时间下课?”
这个班每次上课人都来不全,学生有其他活动就不来上课。有一次课堂上只来了两个学生,马晓飞和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刚刚11岁,在班里年龄偏小,四声音调永远读不对,单词永远记不住,也是令我头疼的学生。那时正临近春节,我打开投影仪,放了几张中国春节红红火火的图片,给他俩讲中国春节的习俗。两个孩子饶有兴趣地听“故事”,马晓飞还时不时和我抢话:“我在学校给我们全班教汉语呢!”我表情夸张地睁大眼睛:“真的吗?”他一脸认真:“真的,全班同学都坐在下面,连老师都坐在下面,只有我在讲台上给他们教。”我脑海里迅速出现这个小不点“上汉语课”的画面,不知道他给同学和老师教了什么,心脏紧了一下。那节课我从收发室借了一把剪刀,从后面装饰墙上取下几片红纸,教他俩剪“春”字,女孩认真地剪着,马晓飞还不会握剪刀,就在旁边打开了话匣子:“我们班同学都说我像李小龙,我踢足球踢得最好,谁都比不过我!”我转头一看:他的发型、眼神真的和李小龙一个样,那种自信和灵气像一束光,瞬间照亮了我。
课程在往下进行,马晓飞在自顾自地玩耍。对于汉语中某些发音来说,初学者简直就是“一锅粥”。比如一读“我去运动场打篮球”就听到“我chu运动场打篮球”,我就得一遍又一遍地纠正。当我再一次让读错的同学跟我读时,听到一声清脆而标准的普通话“去运动场打篮球”从马晓飞口中传出,我向他竖起大拇指。从那以后,每当有人读错,我在纠正时都用眼神示意马晓飞示范,他俨然成了我课堂上的小助手。他有时多重复几遍给别人示范,会露出不屑的神情,有时也表示理解:“大人就是学不会,我在家教我妈妈,她也学不会。”
下课后我往外走,路过伊万阿姨和马晓飞坐着的沙发,会听到他俩的对话:“今天的课上得咋样啊?”“特别好,老师表扬我了,我是班里读得最好的学生。”我想到有一次我准备好了要劝说他父母先不要送他来了,话还未出口,他妈妈迎着我满面笑容:“马可特别喜欢你的汉语课,每堂课都早早准备好书包,还常常给我们唱汉语歌呢!”我只好把想劝退他的话咽了回去。
学校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举办活动,要准备美食,还要用自己所学的语言说一句话。我设计了使用筷子夹爆米花的比赛,事先发给学生每人一双筷子,告诉他们要回家练习。“六一”那天,有几个准备明年报名的新同学也加入了我们班,马晓飞就一遍又一遍教他们用汉语说那句话,又帮着其他班的孩子夹饺子,很有“主人翁”的范儿。
比赛开始了,孩子们围着一大盒爆米花,有的灵巧、有的笨拙地往自己手里的纸碗夹爆米花,一分钟计时结束,有的孩子碗里只有几粒爆米花,而马晓飞碗中的爆米花都高出了一个尖,这让我很是吃惊。他边夹边用汉语数着“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俨然成为了一场表演,所有人都鼓起了掌,马晓飞脸上露出了“李小龙式的”自豪神情。
我决定向学校申请明年扩招一个班,专门招一个低龄儿童班,让马晓飞当我的“助教”和班长。我深深地自责,让马晓飞这孩子坐在“照本宣科”的课堂里是多么委屈啊!
儿童节的活动接近尾声,我们团队的孩子们身着我定制的服装:黄色T恤,胸前是两个红色的汉字“中国”。孩子们站成一排,齐声用汉语朗诵出那句练了无数遍的话:“值此儿童节之际,我们祝愿世界和平!”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推荐阅读
相关新闻
- 评论
-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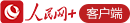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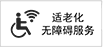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