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字里生出的中华美学精神
中国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华美学精神。农耕文明以土地为命脉,土地更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生命之基。所以中国农耕文明和中华美学精神都可以从汉字“土”开始说起。《说文解字》将“土”动态化解释为土地吐出万物的生命孕育过程,“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丨,物出形也。凡土之属皆从土。”“土”之释义也成为中国农耕文明耕作方式的写照。同时,“土”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核心要素,土与水、火相融,便有陶器和瓷器;土和火、金相佐,便有青铜器,进而化生万物。中国人通过由土制造的器物,展现艺术技能,美化日常生活,更以优美的造型和纹饰赋予器物,象征崇高的天地境界,从而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文化。
古代中国人耕作于斯土,形成九州国土,甚至形成了土地的宗教信仰。《尚书·禹贡》有九州土色,“冀州,厥土惟白壤。兖州,厥土黑坟。青州,厥土白坟。徐州,厥土赤埴坟。扬州、荆州,厥土惟涂泥。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坟垆。梁州,厥土青黎,雍州,厥土惟黄壤。”其中徐州有五色土,《尚书·禹贡》记载其为朝廷祭祀之贡品,“厥贡惟土五色”。如今北京中山公园内的明清社稷坛铺垫有五色土,代表华夏五个方位及五位神祀。中央为黄土,黄帝主居天下正中,有掌管四方之土神辅佐,东、南、西、北分别为青、红、白、黑,对应太昊、炎帝、少昊、颛顼,又分别有掌管春、夏、秋、冬之木神、火神、金神、水神辅佐。土之五色、五方及五神,以一种浪漫化的审美方式呈现出中国人的空间观及信仰观。
中国人视“土”为社神,“土”为“社”之本字,《说文解字》解释,左“示”即神,右为土上生出草木万物。祭祀土地神的场所成为社庙。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有记:“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土中生长之五谷为“稷”,《说文解字》说,田中有禾,人躬种谷。社神为土地之神,稷神就是五谷之神,《礼记·祭法》记:“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社稷二字连用,便是国家及百姓。
土孕育了五谷,更孕育了生命,厚土而厚生,于是就有汉字“生”,甲骨文字形为幼苗正从土中冒出,吐露新芽。所以中国人的生命从土中而起,最终又会回归土地,形成了中国人的自然生命观及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
从汉字之“土”到“社”“稷”,又到“生”,土里生出了庄稼,更生出了中国人在内的万物生机。故而可以将农耕文明塑造的中华美学精神,总结为一种由天地孕育、土地生长的生命精神或生生精神。《周易·系辞传》讲“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同时,土地上的庄稼作物春种秋收,周年往复,构成农耕文明的生生之美。中华美学精神同样如此,生生不息、生而又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连绵不绝、历久弥新的秘诀所在。
中华美学精神又集中体现于中国艺术,故而可从中国艺术中寻觅中华美学精神的农耕之美及生生之美。其实不难发现,诸多中国艺术相关的汉字也破“土”而生,体现出中国艺术和中华美学精神的农耕文明渊源。汉字“艺”的甲骨文字后简化为“埶”及“蓺”,古字形解释颇多,一个人跪着拔草,关联农事生产;一个人执火,关联农事生产或原始农耕社会的祭祀仪式。“埶”字形又发展成繁体字“藝”,上面“艸”部,即草木生长;下面“云”部,表示读音。后来“藝”字简化为“艺”,上面“艸”部是形旁表义,下面“乙”部是声旁表音。这些字形演变都保留了“艺”字的起源与本义。总之,汉字“艺”最初指种植技术或用火技术,二者都同农业活动相关,种植或用火的农业技术又演变成仪式的技术,然后扩散到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六艺”等贵族子弟技能教育,分别是礼仪、音乐、射箭、驾车、识字、算数。《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有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随着社会文明理性化程度提高,文字及典籍的掌握成为文化话语权的象征,所以张法认为“中国古代艺术,形成了以文为核心、以文为最高的有雅俗之分和等级之分的艺术体系。”直到近代,中国古代以文为核心的艺术体系在同西方以美为核心的艺术体系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现代艺术体系中“文艺”和“艺术”并存的独特景观,当下“文艺”一词既指文学是一种艺术,又暗指文学为艺术之首。
中国艺术不仅需要具备形式美,更要体现出以文字为高位的文化精神。汉字“文”的最初或指人的文身,演化为服饰,继而泛指所有仪式的外观。《周易·系辞传下》讲“物相杂,故曰文”,《说文解字》讲“文,错画也,象交文”。天地所生万物的错画相杂亦为文,其实土地之阡陌纵横状又有汉字之“田”,“田”字亦是土地之文。既然文是万物和仪式的外观,自然含有美之义。后来“文”作为普遍的外观之文,削弱了外饰的成分,主要保留了文字的成分,即仓颉所造之文字。文字之美亦为“文”,即《周易·系辞传下》讲的“其旨远,其辞文”。
除了“文”有美的含义,“丽”更可以对标西方艺术之“美”,魏晋时期,曹丕《典论·论文》直言“诗赋欲丽”,诗赋作为艺术文体而区别于奏议、书论、铭诔等应用文体,那么艺术文体的本质性特征在于“丽”,诗赋因其丽,更能摇荡性情,而生缘情绮靡之美。
从汉字“艺”到“文”,再到“丽”,又将回到土地。徐中舒解释“丽”字的甲骨文为上部二耒并耕,下部二犬尾随,“从二耒从二犬。从二耒象并耕之形,古代偶耕,故丽有耦意;从二犬相附亦会偶意。”因此,“丽”字和“艺”字一样,直接和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关联。此外,《周易·彖传》以“丽”释“离”,“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丽”一方面是一种光明普照的样态,可引申为遵从天道而施行教化;另一方面是天地之附丽,或许可解释为草木因日月滋养而从土中生发的摇曳动人之姿态,故而“丽”就成为天地孕育而土地生发出的生命之美,更能体现出一种农业之美。
总而言之,中国农耕文明对中华美学精神之影响,可从汉字中清晰呈现。农耕文明的主要生产方式是耕种土地,形成了中国人的自然生命观和文化信仰。汉字“土”衍生出“社”“稷”“生”等,由此可从文化层面将中华美学精神解读为农耕文明影响下的生命精神和生生精神。中国人在土地上的精耕细作,又产生了艺术之美。汉字“土”又衍生出“艺”“文”“丽”等,由此可从艺术层面具体呈现中华美学精神的农耕文明渊源和农业之美。此外,农业生产不仅看地,还要看天,看天同样是为了庄稼生长等农业生产,故而宗白华认为中国人参天地化育,遵行天文历律安排农事生产,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即“生生而有条理”的宇宙旋律和生命节奏。继而从农业生产到日常生活,全部“融化在音乐的节奏中,从容不迫而感到内部有意义有价值,充实而美。”中国农耕文明与中华美学精神的关系大抵如此,皆可从汉字“土”中生发演绎。
(作者:袁俊伟,系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 评论
-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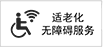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